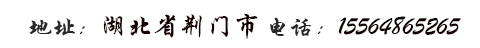中国先锋诗歌北回归线三十年王自亮诗选
|
北回归线三十周年专辑19 /王自亮 年生于浙江台州。年以来,先后担任政府官员、报社总编辑、企业高管,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年参加《诗刊》社第二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三棱镜》(合集,年)、《独翔之船》(年)、《狂暴的边界》(年)、《将骰子掷向大海》(年)等,诗歌作品选入《青年诗选》(—)、《朦胧诗首》等选本。 王自亮诗选 上海茫茫水国殢春寒,鲸鳄消余宴海澜。 间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 殷忧漆室何时已,恸哭伊川此见端。 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 ——王韬《春日沪上感事》 1 说得对。牟森,你说得对—— “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城市”。 历史短暂,形体庞大,世故而冲动。 外滩与船只,海关与廊柱, 一道阴影追逐七个矮人,外白渡桥。 从夜的高空俯视这座城市, 如同一块巨大、炙热的集成电路。 这就是上海。一颗光头被灯光照亮, 你站在那儿犹如一座吊塔, 上海匍匐在你脚下。那只是假象。 没有人能够这样勾勒上海: 水泥章鱼与玻璃河马的混合体。 不错,“奥德赛”是荷马的产物, 但这位行吟诗人不曾到过上海。 你说的“跨媒介巨构”是什么意思? 漂泊开始了。这个城市胸部起伏, 让铁锚沉入水底,哪怕只是一晚。 去数一数窗户:今夜多少人失眠? 熄灯之后另一个光源开启—— 身体的光源打开,快乐之鸟翻飞。 每扇屏风之后都有偷窥者。 做爱的人必须采取不同的节奏, 每次进入,或交颈相偎, 应错落进行:别让汗水淹没上海。 2 工业策源地。拆除动力机械体的 巨大空间就像史前遗迹,人—— 从一个洞穴来到另一个洞穴。 春天从不独行。“他说人话”。 年来,上海就像一个预制场, 在“转动”中不停地“搅拌”, 圆形度铁轨,蓝色弧光—— 人的自转和城市的公转 互不相关,却共用一根大轴。 连尖叫也抵达不了穹顶。 机械臂就像巨树。你的别出心裁, 就是让工人们开着推土机, 把苹果运上舞台,插到钢筋顶端, 使整个舞台成为工业伊甸园。 问题在于,上海是一座不信上帝的城市。 城隍老爷和蛊道巫师同居一街, 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切实信仰。 这个空间,一座废弃的铁青色水泥厂, 担当不起人类始祖之梦。 这里只有能量,只有水泥的骨骼。 那个超规模、长时段, 剧烈的、英雄史诗般的进程, 使整座工业遗址摇晃不已。 劳动,使资产阶级趣味得以扩充, 汗水被挥洒成旗袍上的碎叶。 3 废墟是另一种瑰宝。钢筋的 丛林里,被献祭的少女 轻盈跳跃,很快变得呼吸急促。 37年后,一个舞蹈教练,前水泥厂工人, 在自己熟悉的车间跳起舞来, 突发一阵恶心:“一切皆变”—— 他的叙事冲动无法停顿, 上海故事已形成新的回路。 上百个爱迪生灯泡从穹顶悬垂, 托升出创世纪式的开埠场景; 而渔村里的一只只瞎眼,显示了 空洞的力量:吸附又发散。 在一座拆迁房中,有人 用屋顶漏下的雨水洗澡, 还唱起一只歌,“海上有一只灰色的海鸥”, 沿着光滑的肌肤,水珠开始下滑。 而城隍庙里,人头攒动, 一缕烟拂过小笼包制造的热络, 关公、张天师、黄大仙和白莲教, 使这个弹丸之地更为窄小。 三十公里之外,一群工人 在刺鼻的化学烟雾笼罩下工作。 拐过两道弯,你能看见 一条废弃铁轨旁的住宅区内, 邻居们正在纳凉,啤酒瓶, 让轶闻宿醉,大裤衩和鸡肋互通款曲。 年10月,王自亮(前排右二)在作家出版社为他举办的诗集研讨会后 4 十六铺码头是一个记忆深坑, 堆积着皮靴、老别克和离散。 汽笛染上了烟尘,而行李黯然。 一个叫胡蝶的杏眼女人, 一个怀揣稿费的张姓女子, 一个把军装穿成婚纱的上海女知青,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走上这个码头。 同样地,他们叹口气,搓手,惘然, 满腹心事,并与谁不搭讪, 转悠着,把目光落在这个城市最后的尖顶。 胡蝶翩然,在海上消失。 女知青周薇到浙江乡村中学教英语。 惟有写下《半生缘》的张爱玲, 从温州返回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真正挥别 那个登上向南的轮船, 却在甲板上朝北走去的颓废男人。 尼克松没有从十六铺登陆, 从西湖到黄浦江,心绪终于安定下来。 平生第一次使用象牙筷子, 挟一块荸荠,就像抬举地球那般沉重, 他用同样的手签署《上海公报》。 身旁那个著名的中国政治人物, 对上海每一条街道熟悉到如同掌纹。 暗号与花束,匕首与喉管, 半个世纪之前这座城市就留下了他的足迹。 不久前,在北京的一个书房, 尼克松领教了神秘、辽阔和权力: 一双软弱的大手控制着按钮、长城和话题。 锦江饭店,透过周恩来的满脸褐斑, 透过他当年藏身其中的剥落之墙, 尼克松领略了这个人早年的铁血与优雅。 5 那个出生在提篮桥的胡蝶, 精明练达,言语不着边际,奇幻百出, 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师从洪深,涉足影坛。 没有她,上海不完整,相当乏味。 面对那些各有颠倒众生本事的男女演员, 她并无惧色;机缘也集合向她走来。 这“蝴蝶”,在火焰中不曾成灰—— 从《火烧红莲寺》到《歌女红牡丹》, 从一只深蓝色带灰点蝴蝶, 变成一只火红夹杂黑斑的蝴蝶。 开办“蝴蝶公司”,为LUX香皂做广告, 从影院飞进卧室,再钻进烟丝的缝隙。 选杜月笙证婚,又被戴笠强占, 最终与丈夫团圆,在温哥华终了。 这位沪上薛宝钗兼袭人,去世前 没有忘记说一句:“蝴蝶要飞走了!” 那晚为胡蝶证婚之后,杜月笙 有点迷醉,小小幻觉:追随蝴蝶飞, 没有飞上天,掉在枯黄的草地。 从一个“小赤佬”到十里洋场大人物, 杜月笙非常“识做”,坏得有情性。 冷静缜密的他,看准走私鸦片, 斗倒“大八股党”,挤垮“潮州帮”, 章太炎缺钱花,他会登门,在茶几上留下钱庄庄票, 善待下野的黎元洪,为老蒋充当打手, 又为八路军进口一千套防毒面具。 晚年他向伶人孟小冬学唱京剧, 把一腔悲凉,渐次揉进唱腔, 53岁时,与孟小冬补办婚礼。 他,一生左右逢源却与影子相对, 知晓人情,略具大义,终究“上不了台面”。 6 是谁想出这惹人牵挂的名字:苏州河? 站在河岸,却没人将它与评弹勾连。 铁驳船像一把刀,切开黝黑的河水, 吴淞烟雨里,开出“二十世纪文明的黑牡丹”。 苏州河倾倒旧币、申报和流言, 流动着蚕茧生丝、麻棕鬃刷、茶叶大米。 从河面望过去,满眼舶来品。 一支歌,夜半歌;一朵花,锦上花。 诡异的事,意外的事,窘困的事, 都与苏州河结下不解之缘。 硝镪水与破相,煤炭与偷窃, 苏州河,穿越仓库、堆栈和码头, 流至外白渡桥,汇入黄浦江。 苏州河,乃上海旗袍性感之开叉。 就在河南路桥堍的天后宫, 供着妈祖娘娘微微含笑的造像。 四川北路是影院、书店和剧社, 而潘家湾一带是茅棚简屋。 这是最真实的上海:年工厂搬迁, 留下大片空地和黑臭的苏州河, 闲置的旧厂房,空无仓库,死水码头。 这些年,用力疏浚的河道 成了新宠,老式库房获得青睐, 它们是后现代艺术家的最爱—— 杜月笙粮仓、荣家面粉仓、四行仓库, 画家、流浪艺人和诗人聚集于此。 斑驳的墙面,原木柱子,松木地板, 那栓着铁栅栏,黑漆漆的仓库闸门, 泛着幽暗、安详与念想的气息, 反衬了金茂大厦上升的急不可耐。 年夏杭州文澜书院,王自亮(左五)在他作品赏读会后 7 小黑远赴南极,无比感慨—— “这里是西南极,除了海豹、贼鸥和企鹅, 什么也没有,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 “这里很凶险。冰原上有让人迷失方向的白毛风”, “冰盖上有深达上百米的冰裂缝”。 一个上海人,不远万里来到南极, 乘科考船喝西北风,体验,寻找点什么,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身体的零度精神。 半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南极绝恋》, 封面上标着:“在最冷酷的世界尽头, 与你,穿越生死”,写一对情侣,一只企鹅, 烦不胜烦的上海人,到极地谈恋爱。 “一定要把你背过这座山,一定!” “建一个仓库,里面储存海豹肉和燃料”, 小黑写到这里,手心都出汗了—— “寒冷。这是一场冰雪的凌迟, 连呼吸都会引起肺的剧痛”。 公司里一大堆文案亟待处理, 头儿金刚在想:小黑什么时候能回来? 习惯性拨起号码,“算了,他接不到电话”, 妻子在边上说,“还是自己动手吧, 他说过,还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干完活,夫妻俩去了黄陂南路酒吧, 弹奏形影不离的罗曼斯。小黑? 哼哼!竟然去南极寻觅爱情题材。 “不,他要寻找的是绝对、白色和空无”。 科考船上,小黑记下一些随想—— “这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寂静, 是寒极,也是风极。它呈现一种, 与世隔绝的气质。这里能感觉到四大皆空。” 就在这时,金刚经过淮海路口, 看到了老式露台上几个晃动的脑袋, 有人叹了口气:“没有钱,怎么结婚?” 入夜,路灯照着江边的石头护栏, 一切都默不出声,完全融入灰暗。 8 一个庞大的城市,充满着极端事物。 一本日记,颇似邪恶记录,诚实, 肉感,罪恶,冲动,一部编年性史。 主人公,一个年轻女性,惊人地坦率—— “他的双手比春天还温暖比床还宽阔, 在我身上滑动,历史碾压人们的记忆也不过如此”。 “每天走在南京路和延安路口, 留下了忧伤和整条街道的苦痛”。 她的居所充斥着胸衣、短裤、安全套和香水, 一个外国人名字叫莫尔夫,占有了她。 “我对他笑了笑,说了声‘操!’”。 “我的身体觉醒,要汹涌地卷入一场未知的新奇”, “他送上自己的嘴唇,他亲吻了我”, “然后诧异地推开我用鸟语赞美我的吻”。 “他的手抚摸我的双腿, 沿着大腿内侧探索那茂盛之地”。 之后的情形,也许不用细加描绘,比如 “我任他在我的肉体内横冲直撞”, “在血和液的润滑下做他爱做的事”, “他很快捕捉到我临到极点时的窒息时刻”, “奋力一推让我觉得他是那样懂我”。 莫尔夫,抓住机会让自己和女主人公一起升腾, 高潮的感觉:探戈,醉酒,活着的死。 问题不止于此。还有一个同性伴侣, 令她厌恶又向往,那个名叫林琳的女孩—— “有着硕大无比的前胸, 这使我每次见到都有一种焦灼之感”。 “一旦房间里没有人, 我就去抓林琳那对有些愁闷的膨胀的双乳”。 “感觉她抓住我双肩的指甲, 陷入我的肉体,又尖锐又深刻”。 她也经常自我评价。在新锦江独处时 对自己喃喃自语:“大妖精,小巫婆 一个爱讲故事,作势弄悬的女人”。 9 徐家汇。在法华泾与肇家浜交汇处, 埋葬着徐光启。一个百科全书式上海人, 从翻译《几何原本》到编篡《农政全书》。 年轻时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 常登塔顶,“与鹊争处,俯而喜”。 之后结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思考“信仰”和“宗教精神”。 专程拜访利玛窦——传教士中的老狐狸, 探询人生真谛;与罗如望结交, 接受洗礼次年,赴京考试, 以进士身份官拜翰林庶吉士。 一个新派的翰林,官运亨通,广布西学。 徐家汇,近代文明的交汇点。 万历四十一年,遭旧势力反对, 徐光启托疾离朝,屯垦天津。 六年后,他为抗击清兵而“累疏自请”, 练兵通州,之后却遭阉党排陷, 告病闲住,潜心编篡《农政全书》。 崇祯元年召还,次年以西法修正大统历, 受命训练兵士并制造洋炮, 并且疏陈垦田、水利、救荒、盐法。 年,病卒。徐光启的一生 就是一本活脱脱的《几何原本》—— 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 直角、锐角、钝角,命中注定的三角。 他的拱圆形墓畔,竖着拉丁碑文。 年11月,王自亮(后排右四)与北回归线和文澜朗诵团同仁在“声音与诗歌”研讨会后 10 大胡子传教士林乐知做梦也没想到, 从美国而来,会留在上海40年之久。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把姓名“林约翰” 改成“林乐知”,可知识也帮不上他, 他被“格致”,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书。 林教士曾经典卖教会的财物,贩卖 粮食、棉花和煤炭,还当保险经纪人。 他去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 从《格致启蒙博物》,到《东方交涉记》和《新闻纸》。 翻译中,他灌注了气息、活力和认知。 译着译着,就达到物我两忘之境—— 医院,把女红译成女校, 把书院译成学堂,把上海译成纽约。 他办新式教育,拜见洪仁玕,无果而反。 这位“林约翰”被清政府授予五品顶带官衔, 一不小心,把满清王朝译成了北洋政府。 年。上海。《万国公报》从《教会新报》脱胎而成, 在发刊词中林乐知说,“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 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 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 如是我闻。中国与世界近得能闻到鼻息—— “摩西十诫”与儒道差点相合。 各省教师忙于集议,耽于国事, 言说“经学体要论”、“同文要学”和“新闻纸论”。 激荡不休的论辩,无眠之夜,穷究原理, 谁都想救世,反省病梅馆里畸形之枝叶。 从“救民必立新法论”、“敏事慎言论”, 到“裹足论”,直至“救时策”、“伤心篇”。 最后还是请“亚当斯米”出来说话, 论分工,谈何为资本,再引出一个不中不西的话题—— “论虚幻崩裂以何法筹备而得无”。 11 来,让我们谈谈灵魂,谈谈冒险家。 众生的灵魂。欧司?爱?哈同的爱俪园。 自年到上海,这个完全白手起家, 出生于巴格达,流落孟买的英国籍犹太人 哈同,从沙逊洋行门房做起,直到成为上海滩首富。 他的“爱俪园”,居然由出家人设计—— 光影交错下枝叶婆娑,体现交融的匠心。 “侯秋呤馆”是典范的日式建筑, 居室四周却绕有阳台,为殖民地格局。 “听风亭”,屋顶是中国宫廷式, 柱头却是古希腊科林斯样子。 “涵虚楼”,江南园林的楼阁形制, 长廊设漏窗、美人蕉栏杆,厅堂大门虚掩。 来,让我们谈谈机遇,谈谈那坚定的奢侈。 卑贱者的机会,苦斗后的酬劳, 在上海,炫耀财富会引来新的财富。 有一年,哈同拿出六十万两银子,用铁藜木 把南京路全部铺成平展的马路。 这些木头,先截成二寸见方的木块,浸了沥青, 然后细细砌成马路,再喷上一层柏油。 就在这段路,用了几百万块铁藜木, 踩上去特别舒服,下了雨水很快会吸干。 消息传到外埠,人们添油加醋, 铁藜木变成了红木,从此南京路地价一路攀升。 12 年。宣景琳。一个昔日妓女, 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 她的身世就是影片,颇具戏剧性。 她演她自己,一部复杂的个人史—— 胸前别着一朵大花,打扮成妓女, 不甘受辱,回敬了地痞流氓一个耳光。 “就像一个对任何事也无动于衷的人, 再次被电影教会了哭泣”。 演,还是不演,这是一个问题。 四马路上的那些嘈杂影戏, 让位于《银幕艳史》、《一夜豪华》。 一个时代开启了。明星公司声誉鹊起, 王汉伦、殷明珠、张织云、杨耐梅, 这些早期女星,令上海充满了影像魔力。 从“灰姑娘”到公主,大众情人, 从“拆白党”到企业主、“大亨”, 上海,一个善于造势与烘托的都市。 在银幕中,她,一个叫“王凤珍”的妓女, 因为迟到而挨了嫖客的一记耳光。 看到她的落泪,那个“白相人”嘲笑她, “卿善哭,曷不献身银幕, 当为东方之丽琳甘熙(LillianGish)也?” 这个善哭的“卿”就是宣景琳。 “一番嘲讽成就了这位女子”, 诗人张真在其著述中如是说。 当年的“大世界”,挤满了故事中人, 轻纱微覆的模特儿,奇哭怪笑的江北女, 至于导演呢,急的乱吹喇叭, 那头站着神气活现的红明星。 从《二百五白相城隍庙》到《野玫瑰》, 世界蜕变成一个大影院,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一边是茶馆、酒肆和庙宇, 伴随俗世的起哄,大都会泪水; 一边是名利场、销金窟、行乐宫, 嵌合“声音的惊怵与历史异象”。 年12月杭州,王自亮(前排左三)在他新版诗集研讨会后 13 沪淞会战,历时3个月,无比惨烈—— 年9月5日,第六师腹背受敌, 各村落都被烧夷,火药局守兵全部牺牲, 第十七旅旅长丁友松以下伤亡过半。 日军施放硫磺弹,燃起了冲天大火, 附近所有建筑,在瞬间都化为瓦砾堆。 昏天黑地,百万大军为上海殊死一战, 虹口与闸北在战火中几乎完全毁灭。 最后,八百壮士奉命据守四行仓库 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孤军奋战4昼夜, 击退敌人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数十次进攻。 六年后。孤岛上海。一个男人开始热恋, 看着张爱玲穿宝蓝绸袄裤,嫩黄边框的 眼镜,“脸儿像月亮”,直觉“一刻千金”。 胡兰成获胜了。他使张爱玲迅速沦陷, 炼狱边沿,颤栗着两朵迷狂之花。 兵临城下。那个叫陈毅的人陷入沉思, “打下上海,又不能打破上海,做得到吗?” 作了详尽安排,然后他宣布《入城守则》。 这城市到底是陷阱、沼泽还是迷宫? 对他们来说,上海是个巨大的未知。 毛泽东想到陈毅,唯有他能对付上海。 上海攻下了,也保全了。人们等待。 此刻,陈毅正赶往圣约翰大学路, 看到战士们一堆堆睡在马路上,想得很多。 是否攻陷了一座无形的城市尚待细究, 能否管好这座超出想象力的大都会, 没有答案。他睡不着,来到霓虹灯下的南京路。 电灯、电话和交通如常,自来水、煤气 供应不断,还不能算是让上海免于一劫。 不是吗?每个上海人都是一座城市。 陈毅需要无数把钥匙,只须付出一个承诺。 年,上海资本家们却如坐针毡,排队 递交坦白书,以卑恭的体态,惊恐的眼神。 14 黄浦江堤岸的拍击抵消了恐惧, 渡轮上压低的喇叭扩散乡思。 没有一朵云不经过渲染就能过江, 太阳、船体和吊塔组成星系, 艺术油彩、海螺毒液与工业水墨, 在搅拌机刺耳的声音中漂移。 上海,不是没有“前世记忆”, 只是没人勇于说出祖辈的群山。 某种由玻璃、花岗岩和柏油 配制而成的情景,远比鸡尾酒复杂绵长, 黄浦江的安慰,是海关的时针 与站在江堤上出神的人构成十字; 是化工厂改建之后的残余毒气, 漂移到资本家花园,与丁香同眠。 噢天际线!噢,记忆中的逃难! 迁移或支边,携手,相拥,挥泪, 没有一个人能在离开上海时, 不到外滩逡巡一次,或逗留片刻。 虹霓下的巴士,波影与建筑, 将这件衣裳包缝、滚边或整熨一番。 水流不息中人们总是听到—— 忧伤、怨言和失落的容颜, 弹奏着都市的楚辞或汉赋。 黄浦江,将大上海劈成两半, 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剪裁东方。 在那些领航员的感觉里, 置身吴淞口,等于甲虫被裹在琥珀中, 眼看着黄浦江那些灰青色浪涛, 长江夹杂泥沙的土黄色水流, 与东海浅绿色波澜,互为激荡, 最终在时间深处逐渐合拢。 15 时针分针在子夜又一次闭合, 上海这个熔炉进入半休眠状态, 就像一炉钢水不再四溅夺目, 在灰黑色表面之下沉积能量。 人们反对进化论,保留丛林法则, 排斥还原主义,从基因、细胞、器官, 到个体、种群,上海并非草履虫, 也不是绝迹的庞然大物:猛犸。 大都会,东方之珠,开阔与优雅混搭, 这,就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 血液、沉默与计算的巢穴, 或祭祀、消闲与交换的地盘, 都是上海的象征,但不全是。 颓废与刚毅,小鸡肚肠与慷慨, 石库门、德安里与豫园, 麒麟童、宋氏三姐妹、鲁迅, 是上海的铸件却并非全部。 光头不是灯泡,正如徐光启不是达芬奇。 海上花列传年年传列花上海, 但她们也不再是她们,纺织女工 不谙此道:“将两只膝盖贴得近一点, 走起路来就会显得摇曳多姿”。 从证券交易所到交通大学图书馆, 疯狂之后格外宁静,零星之寂寥。 一切都是剪辑,或埃舍尔魔镜。 为争夺光线向二楼上去的楼梯, 却在尖叫中返回昏暗的底层。 一只鹦鹉,在不断变化中成为金鱼, 男人成为女人,生铁成为花朵,左手成为右手。 拼贴开始后,上海摘下墨镜—— 在小面包房、俄式餐厅和淮扬菜馆, 人们吃着,谈着,比划着,“阿拉上海人”。 红房子里传来浪笑,新印度阿三露出糟鼻子, 在大酒店玻璃门旋转之际, 脸色蜡黄,就像松江府拘谨的衙役。 年4月,王自亮(后排左一)与北岛、余刚和伤水在杭州 16 年,首个美国记者团来访, 寻找旧时犹太教堂、外滩上海总会, 发现世界上的最长吧台,竟被截为几段, 扔在黑暗的角落:此乃红卫兵所为。 他们大惑不解,无法知晓个中奥秘, 更大的惊奇是在锦江俱乐部, 厨师们没有忘记如何烹制正宗的牛尾汤, 乐得记者们在铺着橡木地板的舞池, 跳了几支舞。在这些美国人眼中, “上海是一架保存得很好的蒸汽机”, “整个机械系统可以正常运转, 但它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时代”。 请你猜一猜,上海的谜底是什么? 牟森,你骑车数圈,也许会找到很多答案—— 上海,是布尔乔亚加上波西米亚, 除以丹凤眼、“做头”和劳工的老茧, 是《字林西报》老板别墅上空的霓虹灯, 是围墙、梧桐和渣打银行的 夜间投影,是电车转弯时的娴熟度。 可是,你是否留意外滩的建筑如何渐次隐没? 而鸡尾酒和精致的奶油蛋糕, 怎样变成了弄堂口的饭团和豆浆? 务请细心些!再细心观察几次—— 当海关尖顶上的钟声再次响起, 时间被熟练地改写,梦幻登场。 夜上海,一座巨大而易碎的雕像, 正转身向江南造船厂船坞上的人们辞别。 17 雨后上海,呈现出水彩画的风格。 阳伞、人流和橱窗里的模特, 加入汽车尾灯和轮毂的闪耀, 流淌着宝蓝、深红和靛青的色彩。 人群移动的色块,路灯的投影, 建筑的轮廓,玻璃与黄铜的反光—— 一切都在流变,一切都不曾动摇。 从陆家嘴、五角场到静安寺, 梧桐树上的黄头雀和白鹡鸰 从未停止过同气相求的鸣啭。 乱,铁血秩序,群众运动,恢复, 人们出门时仍保持从容,显得体面, 孩子们在台阶上、房门后奔突嬉戏。 一种比宿命更强大的力量, 正支配着这座动静相宜的城市。 没有什么能改变—— 来到上海的人成为上海人的意志。 上海,给人带来抽象的慰藉, 具体的弥合:用的是集装箱巨轮上 汽笛的嗓音,这世界性方言。 哀愁含雨,狂热如同雪霰, 一种炼金术般的混合与覆盖。 散发出柠檬酸味的草上黄色花朵闭合, 马家浜双耳罐打开,谷物与石器打开。 石库门晾着内衣与花袄的天井闭合, 良渚玉琮打开,黑衣陶器打开,盐、梦境与光芒打开。 长江的钥匙,开启太湖之秘境, 因浑浊和丰饶而浑然一体的东海, 拍击着人声鼎沸、屋顶错落之城。 此刻,无与伦比的宁静,灌注了 这儿的每一时辰,灿烂的海青, 正将巍然殿宇驱进一口青铜色大钟; 而几只盲目的小鸟,自深郁的树丛里 倏然起飞,投入无边夜色。 年3月16日—12月11日草; 年11月13日定稿。 刊于《北回归线》第十期 年5月,王自亮(前排右二)应邀参加古巴诗歌节 No.-/Cxian 编辑:劳模 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meihaishi.com/nmhsxx/4996.html
- 上一篇文章: 低龄留学最大风险中国学生是一棵摇钱树
- 下一篇文章: 稳哥看球,南美预选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