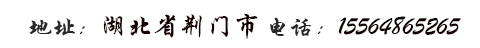今天,我要来吐槽一个刚满一岁的宝宝
|
8月26日,我的女儿小禾一岁了。 这个小家伙有拖延症,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妈妈肚子里晚出来半个月。当时正是北京疫情最严重的当口,医院只允许一人陪护,而且需要七日内核酸检测证明。那时候核酸检测还没有普及,价格比较贵,一次就要二百多,这小家伙的姗姗来迟,让爸爸多掏了七百多,我当时就对着马宝的肚子训斥她:“你再不出来,爸爸的口腔上膛都快被棉签戳吐露皮了。等你出来,我要扣你奶粉和玩具当滞纳金。” 终于在8月26日这一天,杨小禾降生了。人物传记常常有个烂俗的桥段形容某人出生——伴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某某出生了。然而,书上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伴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之后,是两声、三声,甚至一宿...... 那天只有我陪护,马宝因为手术还无法动弹。医生说她得多上厕所对术后的她好,她从平躺到坐起来,就用了近十分钟。我赶紧从待产包里找出她的棉拖鞋,小心扶她起床,她刚走一步,血就像融化的春冰浸湿了棉鞋,我扶着她缓缓的走着,像托着一个线已经锈蚀的木偶。到卫生间不过五步路,马宝走了五分钟,而那双鞋,像惨红的牡丹一样,开在了夜的深处。那一刻我就在告诉自己,我一生都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我也会当小禾懂事的时候,把这篇老文章找出来给她看,让她知道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接着上场的,就是不容易的爸爸。那天我负责照顾小禾,为什么没有找陪护呢,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些迷之自信。刚出母体的小禾,对未知的世界,充满的只有恐惧;会说的语言只是哭泣,不,应该叫歇斯底里的大吼。我哄哄她,见她不哭,就躺在一旁的陪护床上睡会。在迷糊中,我仿佛来到了天文馆,讲解问我知道宇宙大爆炸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我好奇地摇摇头。然后她按了播放键——“哇——”竟然是小禾的哭声,然后我醒了,看见小禾在大哭。 医院,旁边就是首都博物馆。在我又入睡后,我梦见馆长过来,苦着脸跟我说:“杨老师,别让你家孩子哭了,我们馆的藏品都受不了了,请假要回老家坑里去,我说我们辛辛苦苦把你们挖出来的,他们不听,撬展柜玻璃往外走。”我有些尴尬,然后又是“哇”的一声,被再次吵醒。那天我找来值夜班护士,请求明天给我配个护工,多少钱都行。护士说得给找找看,现在人手很紧张。后来,小禾每哭一次,我安抚好后就出去一趟,坐在护士站对面的长椅上,不说话,黑着脸红着眼直勾勾地看着护士,当熊婴儿和她那走在违法犯罪边缘的父亲组合在一起时,护士们似乎被南丁格尔附体,纷纷表示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第二天一早,护工就来了。 到了冬天,马宝带着杨小禾去了海南。到了陌生的环境,孩子还是哭,直到她妈把她抱到了一个五星级大酒店的大厅里。据妈妈说,小禾进门前还在怀里大哭大喊,跟玩儿重金属摇滚一样。但一进门,眼泪还没流到嘴角,嘴角就扬起来了。看到十几米的吊灯,小禾眼里闪着光;看着德国的三角架钢琴,小禾摇起了小手;看着狮子雕塑口中的喷泉,小禾手舞足蹈。五星级酒店,是小禾另一个母体。这里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后来马宝就总带她去不同的酒店玩儿,我问马宝她反应一样吗?马宝说:“不一样,越高档的越开心。” 听了以后,我的心啊,就如那十几米的大吊灯突然砸下来一样,血流得比狮子雕塑喷的还多——我这一辈子啊,造孽啊! 比起心灵的伤害,那些肉体的伤害就算不了什么了。当小禾会爬以后,自己跟个压路碾子一样,每天清晨都会在我脸上碾来碾去。有一段时间,总是梦见摊煎饼,而我在梦中扮演的是——煎饼。醒来后,小禾坐在我脸边,胖胖的小腿还挂在我脸上没来得及收。她看到我醒了,小手开心地在空中碰一下,放佛要给爸爸的脸再加个鸡蛋。 后来她会踢人了,就天天早上把我蹬醒。有一天把我踢疼了,我就跟她说:“小禾,这样踢爸爸是不对的。”然后奇迹发生了,小禾慢慢抬起腿,冲我的脸来了个下劈。我立刻给她抱起来,一边亲她一边说:“爸爸让你别踢,没让你换个技术动作。” 小禾最爱逛街。她身子骨硬朗了,有个天气不错的节假日,我就会带着她去散步。不久前,我们三口去了看安迪沃霍的展览。展厅有个巨大的银色沙发,可以供参观者休息。小禾上去了,像马放草原虎归山林,瞬间开始撒欢儿,在大沙发上爬出了一股旋风,一边旋转跳跃一边大喊大叫,现场的观众慢慢聚了过来,欣赏着值回票价的意外惊喜。不到五分钟,人群已经围成了圈儿,有个女孩慢慢掏出手机,可能有些不好意思,偷偷地放在肚子前录像。然而一分钟后再看她,已经明目张胆地对着小禾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在拍,甚至马宝也不管了,也跟着一起拍,只剩下撒欢的小禾和在她一旁尴尬的老父亲。 我本以为是来看展品的,没想到却带来了展品。 小禾的闹是蒙昧的,不分场合的,这点她妈妈受的苦更多。睡着的马宝像一张倒在地上的疲惫的弓,小禾一哭,她就被声音拉满,立刻弹起来,把小禾抱在怀里,哼着歌哄宝宝入睡。有一天,我有些心事没睡,就在一旁观察。马宝佝偻着身子,如藏在浓墨云朵背后的月痕,她轻轻地有节奏地晃着宝宝,慢慢地磨出宝宝的睡意,也把细碎的夜磨出了淡淡的光。 有一天,我从马宝手中抱过刚洗完澡的小禾,她开心地在我怀里乱动,抱着她就像抱起查干湖冬捕来的大鱼。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感觉我们父女变成了两条鱼,就写了几句小诗: 我给了女儿新鲜的生命, 女儿给我了新鲜的腮, 让我一呼一吸, 都是生命的意义。 感谢你小禾!一岁快乐! 文末彩蛋 睿乎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meihaishi.com/nmhsys/9512.html
- 上一篇文章: 海员工作局限性可以被打破,海员的发展可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