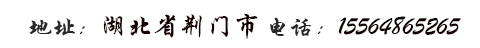爬完雪山,你不做笔记吗
| 下坡路比上坡路更难。这是真的。"入不敷出"通常发生在朝下走。如果你已经四天没合眼,刚刚登临山顶,缓过半口气,想到当天还有30公里路要走,难免心生倦怠。我走得僵硬而缓慢,在自己允许保持的速度的上限。从松碎易滑的碎石坡下降到c1,这一段路我们用了大约40分钟(真的非常伤脚踝,应该多看一些步法技巧的书籍?在山里没有资格抱怨任何路况,但脑子却可以不受控制罢工,做一些随意滑行的弱智举止)。下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骂人,脑筋很清醒,完全明白自己正在因为疲劳而变傻,被一股主观的情绪带动,变得暴躁易怒,我咒骂不应该这么走,多绕出了将近米,从另一个沟槽下到营地。逆风告诉我半夜冲顶就是这么走的,但是我喊他别跟我争论,我对路径有判断,不需要一个前几天开车时没有导航,让我多开出50公里的人指挥怎么走。进山公路他已经走过好多回了。逆风沉默以对,过后一路上我有几次为先前的火气难为情,想开口向他道歉。我没有为自己的恶声恶气解释。进山路上他其实累了,几乎一直闷头大睡,路开岔了,不是他的错。水壶倒不出一滴水,为了减负,出发前我倒掉半壶水,认为完全够喝了,万一口渴,可以吃雪,这段路没有那么多无法预计的状况。在冰崩落石堆中间休息,波哥抛过来一根注射用的葡萄糖,“把它喝了”,我回道,“我只想喝水”,“这就是水”。谢谢他,波哥——不过太难喝了,甜到我想吐出来,我不喜欢甜。在营地仓促吃完半碗粥,1点半出发,全员赶在当天回到子梅村。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跟不上,就在回去路上的BC帐篷里睡觉,我要背上自己的睡袋充气垫和一天的路餐,他们同意了,其实谁都不希望有人落单。我其实不打算真这么干,一定要下山。队伍里唯一的女队员做出特殊示范,让大伙担心,这不好。没有心思收拾行李装备,拆帐篷,我强迫自己一件件干,但还是把一些东西潦草地塞进这个包那个包,有些包随上来接物资的马匹驮下去,我仔细地清理一遍意外状况下必须用得着的物品,随身携带。老陈的手越肿越厉害,嘴皮乌青,他放弃了凌晨冲顶,头重脚轻的忍受高反,他的状态一直不算好,只是没有像另一个人半夜发烧,被迫下撤。一个从来没有户外行为的人,努力走到海拔米的c1位置,已经值得鼓励和赞扬。虽然他很娇气,一路要求骑马,最后爬升c1的长距离陡道,他骑在一匹驮包的马上,从山谷另一侧赶上来。我觉得他做到了自己该做的。夜里,听着他的呼吸偶尔夹杂咕噜声,我摸索打开头灯,还好,他只是鼻塞难受,没有发烧。我的隐忧不是过于谨慎,回来不久,看到一则令人哀悼的消息,7月30日,他念他翁,一名走过高原,户外经验丰富的山友,由于高反在睡梦当中去世了。上山的时候,每一天要走的路可以通过轨迹,做计划,分配好,如果某些地方走得比较艰辛,每个人可以灵活调整,把目标剪成一小段一小段,以此激励自己一小段一小段完成。就像禅修,徒步很容易跟一个简彻明了的正念连系在一起。可是下山的时候,所有激励都消失了,就算你成功完成了预期目标,还是会在回去途中产生一股自讨苦吃的消极想法。世界上不存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人总会被各式各样的心理困扰。现在我要攻克淡漠,鼓舞自己,徒步登山,对人的塑造最为彻底,得到了经验,完成了改变,更坚定更理智,更富有激情,其中哪一项都值得oncemore。厚衣服全部塞入驮包,有一段路乌云迅疾聚拢山脊,把我笼罩其中,雨点噼里啪啦打下,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穿少了。老陈边走边等驮他下山的马,这匹马会从大本营上来,因为我们租了多吉家的马匹,他没有多余的马可供骑行,这匹马的主人开了一个在我看来很不礼貌的价钱,老陈同意了,以元一匹马的价格下山。他提议我先骑一段,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我摆摆手,打算完全靠双脚完成一次登山,自立自破说不过去,而且如果我上马,价钱肯定会蹭蹭上涨,在这些地方十元钱可以花成一元。逆风陪同老陈走在最后,我全身罩在一件老陈的斗篷雨衣里,渐渐跟他们拉开了距离。有一段沿洪溪下降的碎石路,我一个人走,太阳又从云层中快速游动出来,热辣地晒到头顶。整个人裹进厚实的雨衣,虽然防晒,但我意识到在里面越走越困,随时会睡着——实在太渴望睡觉了。马上警惕,把雨衣帽子掀开,风吹在脸上,舒服多了,我在沟槽里寻找马道,尽量踩在其上行走,这些路况相对有弹性,可以保护我还要依赖很多年的膝盖,谷里的冰川湖在下方闪烁幽蓝的光泽,没有看到马道的地方,我就返回流水的碎石坡,再从矮灌木丛中找可以接得上的马道。远远看见两个非常小的影子在河滩,底下似乎有人在等我。下到河边,是波哥和阿飞,我不知道逆风远眺我一个人走在前边,用对讲机通话,要他们接我。河水又涨高了,两人要帮我过河,但在行动以前我跳过了淌急的河水,左脚一只靴子进了些水,很快,没走多久,鞋子和袜子都干了。我让他俩先走,逆风还在后边,马帮还在后边,不会有问题。他们走后,太阳晒得我头疼,视野里的任何景物都让我神经刺痛,也许是电解质紊乱的信号,我从一个户外公司搭建的白色大帐篷拖出一把椅子,河边坐下,拧开水壶,吃了一包头痛粉。走路的时候,琢磨一些问题,以期下一次遇到真正的问题,可以跟危险擦肩而过。5月份的封山令导致计划延期,我在6月份身体出状况,每天都与莫名其妙的极度疲劳,咳嗽胸闷对抗,很多工作耽搁了,以为是旧毛病找上了门。出发前两周,做完全身检查的结果使我心情复杂,中度贫血,肺部有了炎性大泡——疲惫和消瘦的原因。我要反省自己每天抽烟,跟烟鬼比起来,抽的不多。但我却中招了!而且,难受的气短间歇,我继续抽烟,直到在大本营,才决定戒烟。这次出门的头一天,测血压,依然是孱弱的47-55,意味着特定条件下,身体的携氧能力下降。红细胞3.77,低于正常值3.8。老陈做过气胸手术,吓唬我说如果肺气肿严重了,气胸只有22个小时的急救机会,我问他有没有必要带一根针。不是故作幽默,我心里很清楚,必须处处留神,山上的环境,稍有不慎,困境就会沦为绝境。我决定随时调整,一旦觉得喘就停下休息。为了磨砺自己,头一天徒步开始,我背了大包。这是要反省的事情之一。在大本营,状态良好,等众人躺下,我要应付的问题才登场。失眠让我两晚上没有合眼了,可以预见,后面两天差不多。我有点后悔没有备带安眠药,因为在高海拔上,能够不服用药就尽量不服用,所以这个选项划出去了。果然——睡不着又无聊,我录视频,背唐诗,检验有无高反,导致脑子不灵醒。白天出发,我把大包压在身上,注意到大家的表情,昨晚上有人听见了我尽力压抑的咳嗽。队友执意跟我换包,每隔一段路,会收到询问,有没有呼吸困难,累不累。在c1,可以观察到空气稀薄是怎样影响行动的活力。阵雨冰雹后,雾浓云厚,我睡不着离开帐篷,漆黑当中走出几十米,仿佛置身一颗外星球的某个角落,我享受到地球的寂静,以及异样,空气里缺少氧,那种呼吸不到可以交换之物的窒闷感,这时候每个帐篷里都有嘈杂声。我想起那些关于高反的知识,缺氧条件下,你会不能畅快小便,你会被自己溺死,自然面前,人的生存适应性如此脆弱,犹不如一只动物。我想象亿万年以前,深海遨游的生命形态。两小时后,再度爬出帐篷,夜空晴朗,一切又像平地。血氧数据尚可,我又开始觉得自己短时间内就适应得很顺利,仍然没有做到真正的不自负。良好状况持续到了距离登顶仍有80米的位置,一阵筋疲力竭向我袭来,出发时老陈走了几十米走不动了,等他被护送下去,我又觉得刚换的高山靴在碎岩上脚感别扭,脱鞋换鞋,足足耽误了20分钟,我在乱岩石上摸黑找路,上提下移,太急了,打镐的时候,发现这把镐尖沒有开仞,新买的冰爪也不好用,始终绑不紧(逆风帮我绑了两次效果一样),糟糕的错误使我心头一阵慌乱,知道这是开始,要学习的太多,却没有时间改进,就要硬上,到了这一刻,体能短时间内急剧耗尽,我忍不住大口喘气,耳鸣,眩晕,而且体会到了高反的恶心感。回想起来,我还是有一种怪异的精神力,或者不如说,固执,我进入了一个现今不想费太多笔墨描述的境界,在那里边,我跟她在一起,然后冷静,专注当下。我对自己要求过高了,其实认怂也没有那么难,一想到他们高山班毕业了,而我在雪山面前是多么无知空白,一想到停下,爬升缓慢,给队友造成压力,这压力反过来加在身上,我就着急生气,对自己不满,结果可想而知。洞察到这一点,我试图接纳,伴随深呼吸,甚至有了一丝神清气爽的,每口呼吸都进入肺腑,充盈身体每个部位。又一次交融了。登山是为了领略这样的时刻。当然,我明白,这样的时刻不可强求。马帮一路下来,抵达这片风景优美的营地,老陈坐在马上,看上去春风得意。我跟逆风汇合了,他陪同我,在空旷幽静的大片河谷中央行走。前几天,我觉得几名队友里,他不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他却成了陪我走得最久的一个人。25岁的他惯于在川西的高原上行走,可以轻易把我甩在两三公里以外。体能半透支的我,把原先走过的路在脑子里分为一段一段,以麻木的状态,走平坦容易的段落,遇到过河和连绵陡坡,就把积攒的士气拿出来,驱策自己。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掌握一种在走路时休息的技巧,有时候好像睡着了,两只脚还在走路。不是真正睡着,而是关闭头脑某个区域,轮流运转。即便如此,原本轻松的一些路况,还是变得狰狞,比如做大动作,不能从被河水淹没的小径通过,必须抓住杜鹃灌木朝坡上跋涉,穿过刮人的树丛荆棘,跳跃跨过乱石堆,本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我只能心头一叹,面无表情。都说那玛是贡嘎卫峰中,最容易攀登的一座,只需要初级技术。不从南壁上去,的确如此,但接近祂的徒步线路,在整个贡嘎山区算得上经典,地形复杂,陡峭,河流湍急,而且频繁地过河。逆风经常喊停下来休息,我们休息四次,每次不到5分钟,喝水吃东西。他递给我一小瓶芬达,“在山上舍不得喝的”,我表示回贡嘎寺请他喝可乐,他摇摇头,喊我往嘴里多塞几块巧克力。我唯一的渴望就是睡觉,喝水吃饭不能补充体力,只有睡觉。“你确实睡太少了”。说实话,我并不晓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多睡多吃,而不是靠意念生存。虽然闭上眼睛就能睡着,我还是留意到,周围的一切多么美。斜阳下幽谧的深谷,急淌的河水漫过滩涂,在砂石中间肆意游走,闪耀光芒,不远处壮美的雪峰,秀翠的草地,隐隐传来的马铃声。完全置身其中的感觉。一想到身后的山野没有人迹,我就有种奇怪,放松的自由。在自然面前,展现人狂野的一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这一天跟马帮汇合了几次,高地陡谷,他们走得不快,遇到激流险道,不出所料,老陈只能下马步行,不过看上去还挺享受。他表现出了一些品质,遇到困难不抱怨,懂得幽默,至于体能,可以慢慢训练增加。我以为我累垮了,道路延伸,我却一直在走,不停走。至少没有背负太多,要是背上有30斤,锁骨处磨破了,大腿外侧撕裂痛,喉咙干渴,那才叫折磨。我还是太娇气,长期在野外,以我的脾气和皮肉,还需要很多磨练。脚趾愈来愈痛,每走一步抵到靴子,可以忍受的疼痛,不会像去年那次徒步一样整个指甲惨兮兮的。我问逆风怎么选择一双靴子,一劳永逸解决撞伤脚趾的问题(如果可以,我喜欢赤脚),他说他的脚趾从来不痛。好吧,你年轻,肉厚。他继续说,跳溪,跳石头的时候,他的膝盖也从来不痛。简直要发毛了。我走路都是用跑!圆月升起,在巨大可怖的河水轰鸣声中,我们走回了贡布的家。这条河入夜的凶恶,就像十台火车头同时冲出山谷,已经不能用及腰形容了,戴着头灯过木桥的时候,几乎不可以朝下看,看一眼就有被带走的恍惚…关于贡布,关于此行的一些趣事,暂不多写。我以为饿坏了,食物端来却没有胃口,也没有倒头便睡,精神恢复了一小半,加上当晚终于如愿以偿睡了个好觉,第二天起床,双腿居然没有立时酸痛。我觉得精力充沛,比来之前的状态好了不少。波哥还要继续马不停蹄,带人走贡嘎大环线,早上6点收拾装备出发,我们来不及道别,但约了下次一起走线。我记住他对我的鼓励,拍拍我的肩膀说,做得很好,一直走,以后还会更好。一个美好的早晨。老陈的手还是肿得像两只馒头,他从不晓得哪个人那里要了四个鸡蛋,三大盘喷香的蛋炒饭,他说是那个人炒的,后来说是自己炒的,后来又说是那个人炒的鸡蛋,他放的米饭,我一时不好评判,姑且算他炒的。回途,一边开车一边计划,哪里有风景,哪里有好吃的,老陈说回康定,搓一顿过得去的。结果我俩去吃了一顿弄刀耍叉的西餐。完美契合他优渥的气质。下山,吃牛肉火锅,吃烤鸡,吃烧烤,属于正常操作,身体疯狂需要蛋白质。在山里呆一周,时间不长,但是跟店员说冰镇拿铁加份奶油的时候,我突然想笑,文明离我们还是太近了,现实更容易让我满足了。我去餐厅洗手间转了一圈,回来跟老陈说,水龙头里是热水。他说,你喝了一口?我居然没有反唇相讥。我用热水洗了脸。回途是愉快的。傍晚7点,夕阳余晖中,一条激流在公路右侧奔淌,我从反光镜里望向远方山巅的云霞,似曾相识的景象,唯一不同的,是原本属于我的一些东西,从我身上剥落。如同镜中一条细线的公路,我朝前开,离它越远,目送它沉入了孤寂。那是一股长久的忧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meihaishi.com/nmhssh/7812.html
- 上一篇文章: 古代的石雕狮子有哪几种作用
- 下一篇文章: 风水瑞兽之狮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