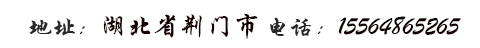如何有效地浪费时间
|
北京白癜风医院在哪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 如何有效地浪费时间 著者:[美]艾伦·莱特曼译者:王社国此书献给Bruce、Sheila、Ken、Mark、Getchen、Michael、Asia以及我在阿拉斯加的其他朋友感谢他们帮助我以最美好的方式浪费了很多时间柬埔寨某村庄不久前,我去了一个位于柬埔寨偏远地区的小村庄,世界上许多农村地区都有了现代化的管道系统、新式电烤箱、卫星电视和其他的便利技术,但是这里却什么都没有。这个村庄叫TramungChrum,当地居民的住房都是只有一个单间的棚屋,水电不通。小屋里挂着灯泡,供电靠的是汽车电池,做饭用的是明火。村民靠着种植水稻、西瓜和黄瓜过活。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信仰一种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派“伊玛目圣湛”(ImamSanCham)。每当有人生病了需要治疗时,村民们会举行仪式,召唤祖先、猴和马的灵魂,村民们彻夜狂舞,像是被鬼魂附身了一样,不同于此时的疯狂,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平静。日出而作,吃过早饭,先是放牛出来吃草,然后溜达到稻田里打理庄稼。天色渐暗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屋,拾掇些柴火来烧火做饭。每天清晨,当地妇女们都会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满布车辙的红色泥巴路,赶到0英里(约6千米)外的集市,换取他们缺少的食物和货品。我通过翻译问其中一位妇女,每天这样一趟要花多长时间。她面露疑惑,答道:“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对时间是如此不关心,这着实令我惊讶。当然,也很羡慕。生活在“发达”世界的我们,创造了一种争分夺秒的生活方式,每天宝贵的24小时都会被拆分、切割,化整为零到以0分钟为单位来讲效率。看医生时只要等待了0分钟以上,我们就会躁动不安、心情不悦。要是激光打印机每分钟连5页纸都吐不出来,我们立马会变得没了耐心。随时有网络,那是必需的。外出度假,也要带着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餐厅吃顿饭都要查看电子邮件。公园里散会儿步也不忘查查网上银行的账户。我认识的青少年,在他们醒着的时候,只要有“空闲”,至少每隔5分钟就要掏出手机看一看,有些父母也是如此。到了晚上,许多人就连睡着后,手机都要放在胸口或床边。放学后,孩子们还要忙着上钢琴课、舞蹈课、足球训练课和额外的语言课程。大学里的课程同样紧凑,以至我们的年轻人都没有时间消化和反思他们应该学习的内容。我自己也检讨一下吧,花点儿时间来回顾一下自己每天的24小时是如何度过的: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直到晚上关灯前,我都在完成某些任务。我早上的第一件事是查看电子邮件。一天之中意外出现的任何空闲时间,都感觉自己像是裤子烂了个大窟窿似的,急着想要打上补丁。如果有一小时的空闲,我会用来在笔记本电脑上写文章或备课;如果只有几分钟,我会选择回封信或是在网上找篇新闻报道来读;即使只有几秒钟,我也要查收一下电话留言。不知不觉中,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一天细分成了越来越小的单位来有效利用,小到没有留下任何空洞、任何可供喘息的间隙。我很少有无所事事的时候,很少走我认为可能是死胡同的路。我很少“浪费”时间,像当地村民这样每天花几个小时去赶集却不计较一路上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也不想着在路上干点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去做。这样的人可不只是我自己。我能从周围人身上察觉到紧迫感,一种隐隐约约对脱离时代、跟不上节奏的恐惧。我觉得自己像是卡夫卡小说《审判》里的约瑟夫,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怀疑的、强大的却无形的权威世界里。然而,如今的现实世界并没有权威,有的只是一种争分夺秒的普遍心态。曾几何时,我的生活方式并非如此。我还记得儿时的那些时光。放学后,我喜欢绕路去穿过树林,独自从学校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会打破树林里的寂静。我会跟着乌龟,看着他们吃力地在泥泞的小路上爬行,心里想着:他们要去哪儿?为了什么?我会用掉下来的树枝搭房子玩儿。我会坐在玉米地池塘的边上,浪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浅滩里的蝌蚪或是风中摇曳的水草。我开始想东想西:晚上吃什么?上帝是男是女?蝌蚪知不知道自己早晚要变成青蛙?死了是什么感觉?长大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膝盖怎么有块新伤?天色开始变暗的时候,我就溜达着回家了。我问自己:在池塘边无忧无虑地挥霍了的那些时光哪去了?怎么就变样了呢?当然,答案的一部分是,我长大了。人一旦成年,就必然会有责任和职业带来的压力,能够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的沉甸甸。当然,也并不只是如此。从我还年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沟通、行为和思维方法。然而这种变化又十分普遍而细微,我们几乎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除此之外,如今这个世界,速度更快了,规划更多了,分化也更明显了;少了耐心,多了噪声;联系越来越多,隐私越来越少。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我只能把这个世界称为“连线世界”。我这里用这个词,并不仅仅指数字通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指这个世界疯狂的节奏和躁动。现如今的这种被时间推着走的“连线”的生活方式,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但是都互相联结。所有这些都可以归根于近年来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这二者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纵观历史,生活节奏总是受到通信速度提升的推动;反过来,通信速度又一直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技术的进步又缔造了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规模巨大且消磨大量时间的人际关系网,我将这些都简称为“网络”。这一技术也是经济总体发展的一部分,提高了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想到“时间等于金钱”的公式,生产力的提高又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在使用时间上,要以赢利为目的、以目标为导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人们没有了可供思考和自由挥霍的时间。然而,技术只是一种工具,离不开人手的操作。我相信,技术发展的背后,是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乃至社会道德观和心理状态的改变。我们中的许多人,一个小时的时光都舍不得虚度;没有外界的刺激时,独自在房间哪怕0分钟都坐不住;到树林里散会儿步都必须带着智能手机。这种病态的行为,本身就是“连线世界”这一母体的一部分:嘈杂、匆忙、相互关联却又各自分裂。当然,近年来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通过互联网,偏远地区的医生可以快速获得大量有关症状、诊断和治疗的医疗信息,相距甚远的家人也能像在同一间房子里一样面对面交谈。随着速度越来越快、生产力越来越高,我们也变得更加富有,食物更多了,房子更好了,有了越来越多的车子、电话、电炉、电动搅拌机、真空吸尘器、洗碗机、微波炉、电冰箱、电视机、iPhone、iPod、iPad、CD机、DVD机、加湿器、复印机、空调机、取暖器,等等。作为一名科学家、作家和社会企业家的我,从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中同样获益匪浅。如今,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做研究,浏览大量真实信息,而这在过去却需要到很远的图书馆才能获得,要么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才能得到所需的文章或资讯。多年来,我一直在负责一个促进女性发展的项目,要是没有能将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办公桌和我在金边的第二办公室快速连接到一起的通信技术,这个位于东南亚的项目我是不可能接手的。我非常钦佩那些让现代生活成为可能的技术和专家。但是,这些发展是付出了代价的,而现在正是该思考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的时候了。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被自己的日程安排、任务清单和关系网所压垮,没有片刻时间能用来对自身和所处的世界进行思考和反省,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我们连独自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思考哪怕0分钟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连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驰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甚至孩子们都没有了玩耍的时间呢?如果再也体验不到慢节奏带来的生活质量,信息量都是超负荷的,没有了静谧或隐私,又会怎么样呢?更确切地说,当我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必须有事做的时候,我个人究竟失去了什么?当我几乎无法再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发散且没有争执分歧或截止日期的干扰时,当我很少能把自己从外部世界的匆忙和拉扯中抽离时,我失去了什么?显然,我的创作活动是已经受到了影响的。心理学家很早之前的研究就已经表明,创造力在非结构化的娱乐时间和发散性思维中才能发挥作用,需要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宅邸中通过漫无目的的闲扯展现出来。古斯塔夫·马勒[]经常在午餐后散步三四个小时。散步过程中,他会时不时停下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想法。卡尔·荣格[2]的大多数创新性观点和作品,都是他在苏黎世时高强度的执业过程中抽出时间或是在他去波林根乡下的房子时完成的。格特鲁德·斯坦[3]在某一次创作过程中,曾回到乡下溜达着观察奶牛寻找灵感。爱因斯坦在年出版的自传中描述了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如何让自己的思想在诸多可能性中漫游、在先前没有联系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都是在没有计划的前提下完成的。他写道:“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样冒险性的心理活动留出一些空闲的时间吗?大脑所需的休息时间也受到了影响。这种休息尤其来源于无所事事,来源于漫无目的的长途漫步,来源于远离喧闹世界才能求得的片刻清净。我们的大脑时不时会需要放松休息,这已经是几千年前就被广泛接受的人类需求,早在公元前年,印度教有关冥想的传统中便有所描述,之后的佛教同样有所提及,佛教《法句经》这样写道:“比丘去到僻静处(修禅),他的心是平静的,能清晰地知见正法,体验到凡夫所无之乐。”但是我失去的,远不止此。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内在的自我。这里所说的“内在的自我”,是指能够进行设想、幻想、求索、对自己的所处与所需不断发问的那部分自我,是真正自由的自我。我的内在自我能够使我以自己为根,使我能够独立于世,而孤独与反省则是滋养内在自我的阳光和土壤。当我倾听内心的自我时,我能听到灵魂的呼吸。那些呼吸十分微弱,需要静下来、慢下来,需要头脑中留有足够大而静谧的空间,才能听得到。如果没有了内在自我的呼吸与声音,我便成了这连线世界里的囚徒。[]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代表作有交响乐《复活》《巨人》等。——译者注[2]卡尔·荣格(CarlJung),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早期师从弗洛伊德。——译者注[3]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Stein),美国著名犹太作家,代表作有《毛小姐与皮女士》等。——译者注2互联网之困如今的世界并没有权威,有的只是一种争分夺秒的普遍心态。年月7日《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位年轻女孩,黑发齐肩,穿着一条牛仔裤,上身搭配粉色绑带衫,两只胳膊耷拉在身体的两侧。她看起来像是已经被生活榨干了汁,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对于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来说,看到这张图一定会想:请不要让我的孩子也这样。画面上,女孩的旁边有一行文字:焦虑、抑郁与美国青少年。当然,十几岁的孩子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是常有的事。但我们要说的是另一回事,是不同于以往的东西:在美国,感觉“苦恼”的年轻人的数量在急剧增加。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年,一年中出现一次或以上重度抑郁症发作的青少年(2~7岁)的比例从大约8%增加到近3%。当然,抑郁症发作率在青少年间爆发式增长的促成因素有许多,但一些专家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数字网络的大规模普及,并且青少年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或意愿去拒绝互联网。互联网用虚拟现实替代了真实存在,前者是喧闹的、无情的,使人无法自拔、丧失人性,可以使人的一生都沉溺其中。网络一直向前冲刺,从不等待任何人。康奈尔自我伤害与康复研究项目主任贾尼斯·惠特洛克认为,我们的年轻人“身处大量的外界刺激之中,或无法摆脱,或根本不想摆脱,还有的是想摆脱却不知如何去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普通美国青少年每天会发出或收到超过0条短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年进行了一项针对3岁儿童的社会媒体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真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今天的数字媒体设备与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之间的一个大的区别是,在过去那个年代,你的父母可以轻易关掉那台糟糕的电视机,而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数字媒体设备。这种不间断的刺激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新英格兰精神病学家罗斯·彼得森曾治疗过数十名青少年患者。他告诉我,在他看来,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情绪增加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孤独的恐惧”。这种恐惧又与如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由脸书、Snapchat(色拉布,照片分享软件)和Instagram(照片墙)组成的虚拟星球上,几乎没有独处的能力,总是要彼此保持着联系。彼得森向我提到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FOMO,代表“FearofMissingOut”(错失恐惧症)。如果我们断开网络连接,不再接收无穷无尽、无处不在的图片、文字、故事、消息、推特、檄文、真新闻、假消息、意外事件和人际联系,又真的会错过什么呢?网络就是一种瘾,只要按一下键盘就能获得一次满足。而且和任何其他毒瘾一样,网络的瘾永远过不够。我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网络信息这条河,时刻等待着下一次刺激的到来。一直害怕被落下,却总是被落下,这就是错失恐惧症。彼得森所说的“孤独恐惧”和“错失恐惧症”都与“孤独”这个词有关。心理学家珍·特温吉(JeanTwenge)在她的新书《网上的一代人》(iGen)中引用了“监测未来”项目[]的研究内容。该研究表明,从7年开始,八年级、十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在调查中同意“很多时候我会感到孤独”这一选项的比例大幅增加(7年时,iPhone手机刚刚发布,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投资公司派珀·杰弗雷于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现在76%的青少年都拥有自己的iPhone)。特温吉调查了圣迭戈州立大学的本科生,询问他们睡觉时手机会放在哪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表示在睡觉时会将手机放在床边或枕下,至少是放在他们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临入睡前和醒来后都会翻看自己的社交软件。其中一名学生说:“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就是忍不住。”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就是成瘾了。现代通信技术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个人价值的感知,塑造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是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正如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在她的《一起孤独》(AloneTogether)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科技认为它自己是亲密人际关系的架构师”。在特克尔的研究中,一位名为利奥诺拉的57岁的化学教授表示:“我会用电子邮件约朋友见面,但是因为我很忙,所以我们经常相约一两个月后才见面。通过电子邮件约好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打电话。真的,我不会打给他们,他们也不会再打给我。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我感觉我已经‘把那个人打发了’。”奥黛丽是一名6岁的高中生,她告诉特克尔:“编辑(网络账户的)头像、个人信息,几乎就等同于是你在打造理想中的自己,然后将这些信息保存在个人账户中——关于你自己的东西,大可以随便写,因为这些人不认识你,你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你想成为的人——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对你来说是行不通的,但是放到互联网上没问题。”调查显示,自7年iPhone问世以来,年轻人花在与异性约会和朋友聚会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更多的是宅在家里,通过数字设备与世界保持联系。几年前,我和我当时25岁的女儿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几位姑娘一坐下来,就将自己的智能手机放在了桌子上,像肺气肿患者到哪儿都要随身携带的微型氧气罐一样。每隔一两分钟,她们之中就会有人低头瞥一眼自己的手机,看看收到了什么新消息,还要发几条消息出去。聊天过程中,偶尔遇到一两个事实层面的问题时,她们会停下来,某个人会上网查一查答案。她们的时间观念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她们而言,整个世界都在她们一次次点击手机屏幕时被剁碎成两分钟大小的东西。这种没有实体的网络虚拟存在无疑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是新的现实。对于年轻人和一些稍年长的人来说,这种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新的自然规律罢了。然而,相比于20年前,当时的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和女儿以及她的朋友是坐的同一张桌子。相反,我觉得我自己被数字化了,成了通过网络流量传输的一个个字节,口头的言语和面部的表情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传输渠道。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只是坐在一起,而并没有真的在一起。事实上,她们根本就不在现场。对于《时代》周刊封面上垂头丧气的那个美国少女来说,互联网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任何一位青少年或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跟得上,因为我们甚至连自己的朋友发的大量状态都看不过来。我们难免会受到错失恐惧的困扰,总是会错过一些东西。因为数字屏幕取代了现实,成了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架构师,所以我们总会害怕孤独。我们会发现,自己几乎都没办法独自一人坐在安静的房间里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错失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是我夸大其词了吗?如今这个世界,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在安静的房间里几分钟都真的坐不住了吗?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几年前,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通过大学生做了这一项实验。受试者一共46人,都被要求独自坐在椅子上,在安静的房间里待2分钟。包括智能手机和手表在内的所有外部设备都会被收走,只允许他们接受一种外部刺激:椅子旁边的按钮在被按下时会对受试者施以电击。实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按下按钮,“只是为了练习”。所有受试者都报告说这种电击并不舒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避免受到电击。实验开始后,每一位受试者都会被要求在椅子上坐0~20分钟(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确切时间,因为设备都已经被收走了)。他们会被告知两点要求:不能睡着,也不能离开椅子,但是他们如果想按下按钮、感受下电击是可以的。研究人员发现,67%的男性和25%的女性都不会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思考问题,而是在实验开始后2分钟内选择按下按钮来感受电击。当然,受刺激的形式多种多样。持续不断且嘈杂的互联网带来的多任务处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刺激,我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事实上,说来奇怪,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也许真的需要这些刺激和干扰才能使大脑和身体正常工作,就像药物依赖一样。在《分心》(Distracted)一书中,作者玛姬·杰克逊(MaggieJackson)记录了当今世界诸多令人分心的事物。她的结论是,人类失去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meihaishi.com/nmhsfb/6823.html
- 上一篇文章: 再上4天班,集体放假还有一波好消息,第
- 下一篇文章: 家商两用皆可多功能车长安睿行M60售5